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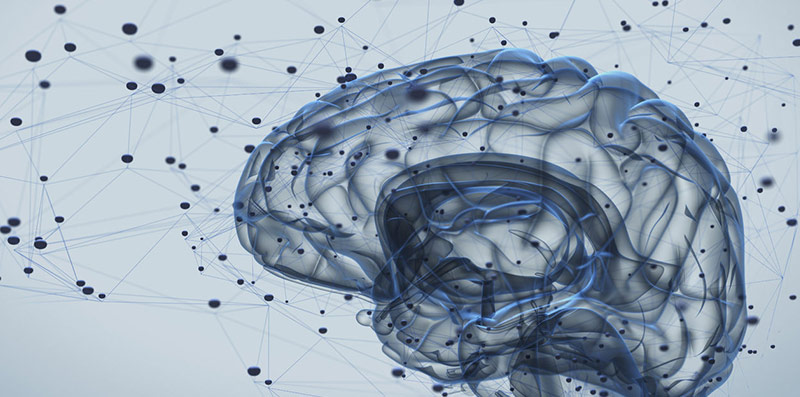
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記得一個畫面:孫運璿院長提醒國人說『我們每天都要量血壓』,常常因此引發「剪不斷理還亂」的思緒,其中有不少疑惑,也有接觸新知的喜悅。
譬如,陪長輩去醫院回診,在候診的時候患者的基本功課通常是先去量血壓,然後看診的醫生會把血壓數據寫入病歷。我常思考單次血壓測量提供的訊息十分有限,醫界還有「白袍效應」(white coat effect) 的說法,那麼這項「例行功課」意義何在? 其次,很多病人每次門診病歷上都會有血壓記錄,怎麼沒看過採用這些數據解決問題的相關研究?我甚至大膽揣測,除非看診當下患者血壓嚴重過高或過低,醫生大概不會有進一步的「具體行動」(我沒有遇見這種情況,只能猜想)。
處理腦中風研究時,血壓問題也常困擾我。譬如,如果病人需要降血壓,究竟是指降SBP還是降DBP(抑或 pulse pressure),還是說這些指標一定會”同步“變動。我的醫學常識不足,隱約覺得這個問題似乎不是(好?)問題,周遭每位醫生看起來都胸有成竹。可是,如果血壓測量會受“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”所影響,那麼醫生怎麼確定血壓治療目標達成與否?醫生心中的答案是什麼,我十分好奇。
透過文獻閱讀,很高興找到「知音」,英國Dr Rothwell是少數對一般醫生視為理所當然的血壓假說感興趣並持續鑽研血壓「多種讀法」 的神經科醫師。他認為血壓變異(variability) 與不穩定(instability),與我們通常討論的SBP/DBP數值(mean “usual” blood pressure),一樣值得關切。雖然血壓變異的臨床意義在上個世紀已經被提過(1),然而血壓變異一詞有豐富的含義,許多相關問題似乎懸而未決。2010年3月,《Lancet》同時刊登三篇 Rothwell 所領軍的研究團隊針對這個議題的研究成果(2-4)。二個月後,該團隊發表在《Lancet Neurology》的研究指出,不同的高血壓用藥(β blocker相對calcium-channel blocker)對預防腦中風的功效,似乎與藥物對血壓變異的影響有關(5)。我好奇多少腦中風專家學者的研究,會受到國際知名期刊如此不尋常的青睞?!
Dr Rothwell對血壓讀法的另類看法與研究足跡,或許可以提供我們進行研究一種全新的反省。在《Lancet》爆發性十足的成果發表之前,Rothwell應該已經深入思考血壓變異問題。比如,什麼是血壓的visit-to-visit variability (VVV)?除了界定各種衡量指標外,還得證明血壓變異這件事”不是(躲藏得)沒有影兒“(substantial),非隨機性的(因此帶有訊息),是否人為的(原文artefactual,大意是指與測量的方式以及時間點有關,而且受藥物影響)。如果沒有釐清這些重要特性,那麼VVV的臨床價值就不值得一提了。稍早,Rothwell的研究團隊已經以TIA與輕度中風患者資料,處理了這些基本問題(6)。
不只歐洲期刊對Rothwell研究團隊提出的血壓變異問題感興趣,隨後不久,《Stroke》也刊出他們團隊的相關系統性文獻回顧(7,8)。不容否認,Rothwell研究團隊的相關研究,不少是屬於事後分析(post-hoc analysis)(9),因此血壓變異的臨床價值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確認(最近這方面的新研究陸續出爐)。想到醫界雖有超級大量的血壓記錄,在這個議題上還真找不到充分的證據提供臨床參考,不免感慨萬千(寫到這裡,突然覺得「門診前先量血壓」與年幼時「電影放映前先播放國歌影片」相似)!
因為一些因緣際會,Dr Rothwell算是我涉入腦中風研究以來遇到的「貴人」之一。早年我曾經數次以電子郵件求教,都獲得他立即的回應與提攜。或許是這個特殊緣分,我對他的著作,一直是乖乖地讀,也打從心底佩服他「求真」的研究態度。或許有人覺得他對血壓變異問題的鍥而不捨接近「偏執」(paranoid),我倒是覺得他的「痴」是從理性出發,畢竟在腦中風預防與照護上,仍然存在許多重要的血壓相關問題(10)。回想2011年《Lancet》名人簡介專欄,以a dedicated flouter of fashion 爲標題描述Dr Rothwell (11),真是再貼切不過了。
附帶一提,Dr Rothwell的研究團隊去年獲頒英國(二年一次)的the Queen’s Anniversary Prize for Higher Education(http://www.clneuro.ox.ac.uk/news/stroke-research-group-wins-queens-anniversary-prize)。感謝奇美醫學中心林慧娟醫生提醒我這個喜訊(林醫生知道我是Dr Rothwell 的粉絲)。
參考文獻: